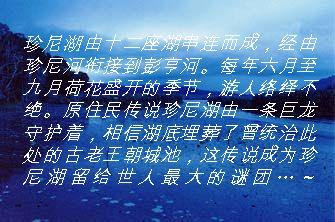~我在珍尼最初的落脚之处~
姐姐打量着客厅里脏兮兮的地板、灰黑像是未曾清洗过的沙发椅套、在屋里自由出入的猫眯、屋角落的蜘蛛网,不禁和我咬耳朵:“你真的要住这儿吗?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喔!”我莞尔。
送别了姐姐和表哥嫂,我们各自为隔天的第一天正式上班预备,查丽雅姐热情地招呼我们享用晚餐。
“伍,需要汤匙吗?”
“伍好厉害!真的不需要汤匙吗?”大家你一言,我一语。
“还好,蛮方便。”我笑答,也不怕失礼就问:“其实为什么你们喜欢以手抓饭?”
“是这样的,回教教义说,我们的手掌上的某些化学成份与食物融合后能帮助消化喔!”白白胖胖很可爱的娜茵笑说。
“原来如此。”老实说,我很高兴饭后不需清洗汤匙,我很懒吧?
不巧第二天我开始皮肤发痒,可能是水土不服吧,不久全身便冒起红点,数日不退。茜玛的母亲趁机向我推荐她的独家秘方:“这药油是我秘制的喔,先以热油炒各种药草,再加食油熬煮好几个小时,不容易制成耶,你试试,很有效。”有鉴于她的盛意拳拳,我姑且一试,不意那药酒果然见效,隔天红点便消失无踪,倒让茜玛母亲得意万分,“没骗你吧?真的很好,我给你一小瓶好了,不能多给了。”“谢了伯母!”